|
蒸汽保温钢管 原标题:周雪光:在中国场景下阅读韦伯为何艰涩难明?| 韦伯逝世一百周年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4.21—1920.6.14) 按:纵然许多人未曾完备读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一书名对大多数中国读者而言依然如雷贯耳。《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德国头号大众知识分子”马克斯·韦伯的代表作品,初次发表于1904-1906年,一经问世便立刻引起读者的巨大兴趣,其影响超出了汗青领域,也使刊载它的《档案》杂志的销量成倍激增,至今被公认为经典名著。在这本书中,韦伯分析了他的紧张观点:新教信仰塑造了人们的伦理规范,沉淀为欧洲社会特有的文化特质和生活方式,成为理性资本主义精神,推动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2020年6月14日是马克斯·韦伯逝世100周年龄念日,译林推出了该书的全新版本,并约请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雪光撰写了导言。在这篇导言中,周雪光不仅总结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对西方世界的深刻影响与紧张意义,也为中国读者分析了韦伯在中国语境之下阅读困难的缘故原由。他总结认为,“这本书讨论的两个焦点问题,即理性资本主义与宗教看法的文化沉淀,均与中国社会文化相去甚远,对于中国读者来说颇为生疏,难以从一样平常生活的身心感觉中领会领悟。”即便云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依然值得一代代中国读者阅读,由于“所谓经典作品,其价值不是那些详细观点或结论,而是提供了一种思维角度和要领,引发读者的想象和思索。韦伯著作正是为我们提供了如许一个视角和要领,唤起了相干的问题意识”,周雪光写道,“我们不停重读经典,不是一再地接受其详细内容,而是将自己的狐疑和思索的问题与经典中的视角和思绪碰撞,以期得到新的感悟启示。” 周雪光 斯坦福大学社会学教授、李国鼎经济发展讲座教授、弗里曼—斯伯格里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资深韦伯研究专家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新译本导言 文 | 周雪光 马克斯·韦伯是十九世纪以来最为紧张的思想家之一,其代表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遍及和深刻的影响。译林出书社的这个新译本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新的阅读时机。 我很兴奋有时机为这个译本撰写导言。我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重复阅读韦伯作品,借以引发理论想象,提炼研究问题,推进学术思索,从中获益匪浅。我从研究者角度与读者交流一下自己的心得领会。 一 巨大的思想通常与巨大的期间携手并行。韦伯从事学术活动的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之间,正逢资本主义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经济情势在欧洲各国确立,重组了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改变了世界面貌和格式。欧洲思想界也因此独领风骚,极大地发展了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阐释。在这个大配景下,韦伯以独到的思绪探讨资本主义的起源,即从看法文化条理着眼来熟悉和理解经济征象,并特别夸大前者对经济活动、组织制度的深刻影响。这一思绪与同期间的其他巨大思想家如马克思、涂尔干等迥然有别,独树一帜。 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始于如许一个观察:在十九世纪前后的欧洲各地,基督新教盛行的区域通常陪同着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宗教信仰与事业精神同时体现在同一类人群身上。由此引出本书的命题:基督新教所产生的职业伦理与现代资本主义有因果关系。韦伯提出,新教信仰塑造了人们社会生活的伦理规范,沉淀为欧洲社会特有的文化特质和生活方式,成为理性资本主义精神,推动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一命题在学术界和思想界引起很大争论,引发了韦伯随后的一系列回应和阐释。这些写作组成了这本书的内容。 韦伯讨论的出发点是区分传统资本主义与现代资本主义。在韦伯看来,市场经济,包括钱币经济,自古即有,但属于传统主义的经济活动:或自给自足,无力扩张;或贪得无厌,冒险无忌。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代产生的理性资本主义亦寻求营利,但体现出理性的谋划方式与生活方式。 韦伯提出,现代资本主义精神来自奇特的带有“伦理色彩”的生活方式,这一伦理的焦点即积极谋划但同时禁欲的情操,即“把劳动看成绝对的目的自己”的“天职观”。蕴含于宗教信仰的伦理规范对小我私人举动产生强有力的束缚,如有违反,则被认为有悖义务。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经济秩序需要对挣钱的‘天职’的这种全力投入”,这一气势气魄( ethos )特别顺应理性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从而成为资本主义之精神,体现在企业家和劳动者双方身上。 这本书的其余篇幅进一步阐释和论证这一命题,以此“探明通过宗教信仰和宗教生活实践所产生的那些生理动力,这些动力为生活方式指明了偏向,并将小我私人固定于这种方式中了”。韦伯特别存眷的是,上述诸环节间的逻辑链条是怎样产生的:为什么新辅导致特定的“天职”职业观;这些宗教看法如何转化为伦理而塑造人们的生活方式;又如何成为理性资本主义精神。 “天职观”起源于十六世纪路德宗教革新。路德将宗教从教会中解放出来,将人们履行世俗职业的义务视为道德实践的最高内容,即“天职”。但路德的职业观将职业劳动与宗教原理分散开来,不主张营利活动,无法挣脱传统主义的束缚。韦伯把分析眼光引向了清教特别是加尔文教派。与路德教义相比力,清教教义规范体现出严肃的现世眷注,以现世生活为己任,与现署理性经济活动密切相干。 然而,韦伯不是停留在这里,而是提出新的问题:清教教义的目的并不是提倡资本主义精神,而是提倡清教徒生涯与事业的焦点寻求,即“灵魂救赎”。需要进一步回答的问题是:以禁欲主义为焦点的新教教义,如何变化为人们一样平常生活的道德伦理,进而体现为资本主义精神的? 云云,韦伯进一步延伸解释逻辑的链条,向深处开掘。加尔文教提出了关于清教徒灵魂救赎的入世克己论,即通过世俗职业劳动来自证为天主选民,由此塑造了人们的“天职”职业观和禁欲举动,依天主之名,行职业使命。这一职业观,在生理效果上将营利寻求从传统主义的伦理屏蔽中解放出来;在举动上则将一样平常生活彻底理性化了。换言之,在寻求灵魂救赎的宗教活动历程中悄然产生了一个紧张变化,即随着这些宗教寻求而来的信心,逾越了自然状态,在微观上转化为人们据以行动的伦理,渗入了人们的意识和潜意识,塑造了人们的理性举动和生活方式。在文化层面上,它们形成了奇特的市民职业气势气魄,沉淀为人文看法、民族气质。韦伯敏锐地注意到,这些文化特质先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而存在。比方,为神荣耀而创造产业的生活方式,其起源可以追溯到中世纪。但只有在禁欲的基督新教中才找到内在一致的伦理基础,推动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那种态度在现代资本主义企业中找到了它最合适的情势,而现代资本主义企业反过来又在它那里找到了最合适的精神动力。”两者相辅相成,成为“庇护着现代‘经济人’的策源地”。 韦伯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的讨论是其西方社会理性化历程理论的一个组成部门。韦伯认为,西方社会履历了一个与其他文明差别的理性化历程,即自中世纪以来的祛魅化历程,从自然、巫教等看法渐渐走向了理性化、体系化的看法体系。理性生活方式使得人们降服自然状态,挣脱不合理的欲望以及对世俗与自然的依赖,使人的行动为长期的理性和伦理所束缚,尤其体现在宗教信仰与经济理性主义的关联之上。比方,天主教的教会圣礼仪式体现了克里斯玛权势巨子,而加尔文教所提倡的世俗生活中的职业劳动则反应了祛魅化的积极。与其他宗教派别相比,新教伦理夸大排斥情感、坚守理性的生活处世;将狂热而朴拙的心田秉性引向在世俗职业生活中追寻禁欲理想,从而转化为现代资本主义精神,推动了西方社会在科学技能、理性组织和生活方式诸方面的理性化历程。 需要指出的是,韦伯并不认为唯有新教伦理才能诱发理性资本主义,也不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只是来源于宗教革新,或者作为经济体系的资本主义就是宗教革新的一种产物。韦伯提出,本书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观点和讨论,也不是这一征象唯一可能的解释,而是夸大两者间有相辅相成的内在关系。这些主张与韦伯阻挡汗青决定论,主张汗青历程的多重途径、多重因果关系的态度是吻合的。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德]马克斯·韦伯 著 林南 译 译林出书社 2020-5 二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涉及一个弘大的主题,即人们的精神活动,包括宗教信仰,如何转化为基本的伦理道德,影响到一样平常生活方式,进而沉淀为民族性格,形成“西方市民阶级及其特质”。处置惩罚这一弘大主题,涉及一系列要领论问题。韦伯在这一时期尤其存眷并致力于发展社会科学要领,本书体现了这方面的一系列实验:其论述气势气魄兼具德国社会科学的汗青主义传统与缜密的理论思辨逻辑,展现出韦伯标志性的比力制度分析、理想类型等一系列要领。 一方面,韦伯受到德国社会科学奇特的汗青主义影响,将资本主义精神发展放在详细汗青历程中考察;我们从文中关于汗青上欧洲各地经济活动以及各教派教义的演变的讨论可见一斑。另一方面,韦伯提出了一系列“理想模子”,比方“传统资本主义”与“理性资本主义”的分类,凸显差别征象的类型特性,通过比力制度要领来条分缕析地剥离各种可能的混淆因素,确定新教教义与资本主义精神间的因果关系。韦伯特别指出,这部著作不是汗青主义的叙述,而是“以一种根据‘理想类型的方式’贯串起来的顺序来展示宗教思想”……以便“在研究它们那些最连贯的情势的时候,发明它们的一些特殊后果”。在这里,韦伯遵照了社会科学要领,以注意逻辑一致性的方式将这些讨论对象加以出现,而不是着眼于现实汗青发展的历程。 在确定了基本命题后,韦伯提出了下面的分析路径:起首找到宗教信仰的某些情势与职业伦理间的特定“亲和力”,然后考察这些亲和力对物质文化发展及其偏向的影响。这些积极试图回答以下问题:现代文化的内容在多洪流平上可归结于宗教动机,即宗教信仰(清教教义)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因果关系。 韦伯比力制度分析的要领贯串全书始终。在本书起始,韦伯比力了天主教和新教与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差别关系,并将这一差异延伸至一样平常生活的差别侧面。比方,怙恃在子女教诲种类上的差别选择显示出差别的精神情势气魄,从而影响了子女的职业观。另外,作为“被支配者”群体,德国的天主教徒并没有走向经济理性主义;而在其他地域,同处“被支配者”职位的新教徒则显露出这一倾向。云云多方位的比力分析指向了宗教信仰特质所产生的决定性作用,而不是此时此地汗青—政治状态的影响。 在随后的分析中,韦伯逐步比力了差别教义的内容,借以辨别哪些要素导致了理性主义倾向。韦伯指出,新教与天主教的区别不在于“禁欲”,而是禁欲与营利寻求同时落实在同一教派之上。在讨论“天职观”时,韦伯将路德教义与加尔文教义加以比力,指出前者躲避现实的出世取向与后者积极入世的理性活动;然后进一步讨论这一看法对营利活动的影响,从差别方面论述这一看法如何导致了价值看法的变化(职业观,赢利正当化)。在随后的讨论中,韦伯进一步比力分析了禁欲教派中的虔敬派与加尔文派,指出前者夸大情感,因此与传统主义更为切合,有助于造就“忠于职守”的官员、职员和家庭手工业者,以及家长做派的雇主。相比之下,加尔文教派的宗教基础更为理性、内在一致,与“市民资本主义企业家的那种生硬正直而又积极的意识”更有亲和性。 韦伯通过这些理想类型的多条理比力提炼,论述了一个紧张因果链条: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体现在职业观上的理性生活方式之上,尔后者恰恰产生于基督新教特别是清教的禁欲精神。 马克斯·韦伯 三 在韦伯的理论体系中,有着久长汗青的中国事一个紧张的比力参照体;这一点在韦伯关于支配情势、权要体制和宗教等一系列讨论中明显可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是韦伯宗教社会学研究的开端,作者将同一思绪延伸至他的《中国的宗教》等研究著作。 虽然本书在西方思想界有巨大影响,但在中国场景下阅读韦伯,这本书尤为艰涩难明,阅读起来“隔膜”颇大。我认为,这是由于这本书讨论的两个焦点问题,即理性资本主义与宗教看法的文化沉淀,均与中国社会文化相去甚远,对于中国读者来说颇为生疏,难以从一样平常生活的身心感觉中领会领悟。 韦伯在另外讨论中国宗教的著作中指出,中国汗青上有活跃的市场经济,包括钱币经济,但这些均属于传统主义意义上的经济活动,没有导致理性资本主义的兴起。在中国,钱币经济不但没有削弱传统主义,反而强化了它。这是由于钱币经济与权要俸禄联合之后,为支配阶级创造了特殊的赢利时机。因此,家产制支配形态下的财富累积,不是一种理性的经济营利,而是一种政治性的掠夺资本主义。由此发展而来的不是汗青上带有市民色彩的阶级,而是“到处伺机于纯粹政治性的官职聚敛”。韦伯进而言之,国度的重商主义规制虽然可以培育生产业,但无法扶植资本主义“精神”,由于中国传统经济中没有现代资本主义谋划的法律和社会基础,而且缺乏制约和抵制权要权利的其他独立气力。换言之,传统的官商联合制度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南辕北辙的。 依此视角来看,韦伯意义上的现代资本主义在中国汗青上从未得到发展的空间。中国读者更多熟悉的是传统资本主义意义上的经济活动,或浸染发展于由此而来的文化精神和价值取向中。这为理解韦伯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讨论带来了不小的困难。 中国读者理解这本书的第二个困难缘于对宗教精神及其在社会生活中意义的生疏感。韦伯笔下的加尔文主义以及其他宗教信心渗出到西方社会一样平常生活之中,成为基本伦理和职业操守,以及由此产生的生理动力,塑造了人们的基本生活方式。韦伯注意到,美国社会中各教派是那些具有宗教伦理特质的人们组成的志愿性团体,经世俗化历程而成为身份象征,在汗青上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新教精神传统与教会正式威权或行会非常差别,提供了现代市民阶级的精神情势气魄以及小我私人主义的汗青基础,并为相应的民主制度提供了基础。今世西方社会文化的诸多方面仍可追溯到宗教信仰的沉淀,虽然这些宗教基本已经隐而不现。如韦伯夸大指出的那样,只有熟悉到伦理背后的宗教渊源,才能真正理解这一伦理的强鼎力大举量。比方今天我们不时听到的关于学者从业天职感的呼声,正是谁人迢遥期间精神传来的回响。 与此相比,汗青上的中国度族社会长期以来提供了基本的组织情势,血缘界限清晰,亲疏条理分明;行动规则多是来自各种脚色关系的相对主义的文化界说。因此,中国读者对于西方宗教传统和相应的文化看法知之甚少,对深蕴于宗教信仰基本之上的习性和价值观非常生疏,几近无从领会。有学者提出儒家士医生文化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联。在我看来,士医生的家国情怀与韦伯笔下的理性资本主义精神是扞格难入的。 再次提示读者注意韦伯的态度:宗教信仰与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不是唯一的因果关系;资本主义经济不存在唯一的发展途径。韦伯意义上的“理性资本主义”不是也不应该是各种文明高低优劣的价值判断。本书的意义在于提示我们,中西文明有差别的发展途径,而文化看法是比力、理解这些差异性的紧张线索:一方面,资本主义精神、理性经济活动、权要组织、法理支配情势等组成西方文明的诸多方面,都可以在其宗教信心中找到渊源。另一方面,这一比力制度分析也启发我们从文化条理熟悉中国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诸方面及其精神渊源。一些根深蒂固的看法习性,如长老制度、等级制度深深镶嵌于文化传统设施中,在中国情境中被自然化或超自然化了,也因此被合理化了。 所谓经典作品,其价值不是那些详细观点或结论,而是提供了一种思维角度和要领,引发读者的想象和思索。韦伯著作正是为我们提供了如许一个视角和要领,唤起了相干的问题意识。我们不停重读经典,不是一再地接受其详细内容,而是将自己的狐疑和思索的问题与经典中的视角和思绪碰撞,以期得到新的感悟启示;经典作品也因此得到新的活力,这正是韦伯理论以及其他思想学说具有鲜活生命力的缘由。 周雪光 2019.11 本文书摘部门节选自译林新版《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导言部门,经出书社授权公布,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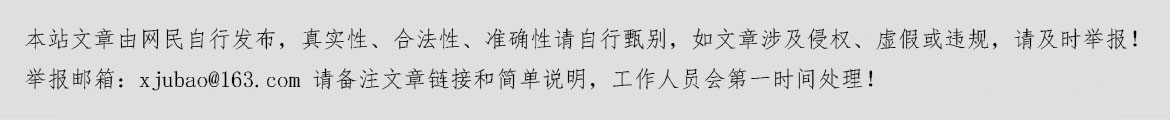
|
 鲜花 |
 握手 |
 雷人 |
 路过 |
 鸡蛋 |
分享
邀请